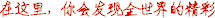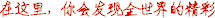舞蹈艺术家,1958年生于云南,洱源白族人,以“孔雀舞”闻名。1994年,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2003年,杨丽萍任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总编导及主演。在2012年央视春晚以舞蹈《雀之恋》,再展舞蹈诗人的风姿。
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记忆为她的人生启幕,“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经历十年“文革”,她骨子里流露着悲观,“我对人性很悲观,我很警惕”;四十年舞蹈生涯,她自称守望之人,“小时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她说,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对我没意义。她,就是舞者杨丽萍。
我对人性是悲观的,我崇尚自然现象
问:除了自己个人生活以外,我看您很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针对一些社会议题您是什么态度
杨丽萍(下称“杨”):不太想去,但我对人性是悲观的,因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非常警惕,我很警惕,像孔雀一样警惕,小心,因为人是最可怕的动物,要不杰克逊就不会死了。
问:1971年进入版纳歌舞团的时候,正值“文革”。
杨:所以看到很多,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一样的。现在随时人都会伤害你,他们甚至伤害你不知道为什么伤害了你。
问:那个阶段会在你身上留下什么样的政治印记
杨丽萍:不光是“文化大革命”,现在一样的,只要你给人機会,给他时间、土壤,说现在可以放火了,你看他就会到处放火了,现在没人管没法律了,他就开始砸窗户了,他就开始拿着機枪扫射了,所以我很悲观,人很复杂。
问:您觉得这种复杂是什么
杨: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打开了,什么都出来了,苍蝇、蚊子、孔雀全都放出来了。
问:这是不是也影响了您对婚姻和归属感的理解
杨:我很崇尚自然现象,大企鹅养一个小企鹅,它可以一个月不吃东西,然后把它养大了,小企鹅长大了就走了。企鹅与企鹅之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它们也有集体,它们也有一个个体,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不太喜欢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一些规定,约束,我那个《孔雀》里面的第一幕就是鸟笼,我在上面,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由。
跟孔雀学着做人,尽量去奉献
问:在您的理解中,婚姻只是一种关系,一种契约,凭需要来取舍它的存废,不必太过纠缠,那人跟人的这种关系是否构成责任
杨:在这个社会上很难,很难跟人相处,就是要以善待人,尽量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尽量不要索取,比如说兄弟姐妹,你给予别人的东西,你不要想他要夸奖你,说大家对我很好,这个不需要。
人要找到一个爱的感觉,跟一个人相爱,然后那个人就会要求你,你就要有责任,所以你一般都简单一点,尽量去奉献,我的态度就是,基本上就是尽量去奉献。比如说我要去哪里演出,就按我的想法,我就会说我来演出,他问你需要多少钱,你的演出费多少我说你出个价吧,我不会出价,你愿意出多少,我觉得合适我就去,不合适我就不去,就不会去给别人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你可以选择不去。
问:您排斥这个吗
杨:我不是排斥,我看到事情的真相,都是太多利益的,对我来讲没有意义。我喜欢用舞蹈,用艺术,用精神跟人去交流,而不喜欢用一些这种七七八八的东西。
该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这个度,不能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个社会隔绝,也没必要。希望我们永远在原点上,世界再纷乱,再乱,你永远不去绕圈,你永远在最原点,你肯定要去慢慢转,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出生地就是始发点。
人太复杂,其实我们就是一棵小草
问:谈谈您的价值观。
杨:就是特别像自然里的。
问:还是要回归到自然。
杨:一棵树长大了,它长起来了,能让你呼吸到氧气,然后它给了你绿荫、清凉,然后它自己是靠着阳光,靠着大气存活。只要你不去砍它,人为地把它砍坏,它自己就会生长,然后这就是它的价值。但它为什么要长那么大,没人知道。你去问那棵树,或者问太阳,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光明,是我们要给你钱吗你照亮我们,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太阳的价值观,月亮的价值观,包括一棵树的价值观。
我们人太复杂,其实我们就是一棵小草,你想宇宙有多大,我们根本就是一个小细胞。我们用光的速度都找不到宇宙的尽头。然后我们好好在这里,我们一个生命最多一百年就逝去,然后再生长,世纪永远在更替,从发芽、开花、结果、掉叶子和下雪,然后再发芽,都是在轮回。太短了,人的寿命太短了。所以这么多东西我就不想去想,因为太没用。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不想去把它说清楚,如果要用文字说清楚,就像我怎么去比喻这么一棵树,或者太阳。
问:您从什么时候有的这种体悟
杨:我就是从自然里学的,就是跟那些僧人学的,跟孔雀学的。我要是有个孩子我也不会强迫孩子做任何事。我现在没说你必须要上学,你想学这个你就学,我会指导她,跟她谈,平等地谈,而不是强迫的,然后尽量地给予她,然后在她身上发现她,告诉她,让她找到自己,这个就是我的方法,这个很简单。
不是商业而是生存法则,灵魂也要吃饱的
问:外界对您还有一个评价是“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商业和艺术,最难兼容的两个事情,在您这里似乎得到完美的结合
杨:我们是在原点上,我们在始发点,我们也在终点,我从来都在这个点上,所以我是特别清晰地知道。在2000年以后,人们知道一个电影要拍出来一定是要有票房的,2000年以前就是谁爱票房谁不是艺术,你看现在人才明白。我跳《雀之灵》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这个舞蹈出来以后,跳出来以后一定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人需要的,是可以买票来看这个作品。
所以我2003年演的《云南映象》一样,走到哪都是票房,从舞蹈门类票房上没有问题,这个是一种生态的平衡。你说我们一群人跳了半天舞蹈,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体力,我们跳舞是要花体力的,我们跳了那么多,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灵魂有了寄托,然后我们跟人没有关系,这是欠缺的。就好像太阳出来没有用一样,我们太阳出来,太阳升起来一定是它跟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的宇宙,跟我们的地球是非常的相关。
我们是舞台艺术,我们不是小时候的,在篝火边上自娱自乐,我们只要一进到剧场,我们就会是一个仪式,宗教,舞蹈宗教。人是要信宗,有信仰的,观众就是信仰,也跟我们一样信仰,所以他们来看我舞蹈,所以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就是舞蹈是我们的信仰。
这不是商业,这就是一个食物链,是一个生存法则,因为人们不单是要吃饱肚子,灵魂还要吃饱。比如说我们在台上跳舞,观众灵魂没有吃饱,所以你必须是又要有精神的,又要吃饱肚子,这是个特别简单的,这不是商业。这叫一个非常和谐,很生态,我们活得很生态。
问:现在有“出书热”,您本人好像从未出过书,为什么
杨:你要出书,就像跳舞是你擅长的,出书不一定是你(擅长的),出什么,有没有意义你只是为了出一大堆书,然后不停地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