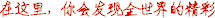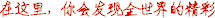天长地久总有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王安忆的小说借用了白居易的诗词最后两句的颈字的提名,讲述的也是关于女人从生到死的情感的故事,因感情而红,因感情而死,仿佛红颜薄命是不可违背的命运,只不过,王安忆带给我们的王琦瑶,更多的是红颜薄情,情的淡泊和消逝,命和存在也没有了意义,尽管王琦瑶在面对着男人要么背叛、要么无能,依然没有封闭起大脑中感情区域中的功能,依然怀有对爱情的向往,但是,没有了选择权或者说早已放弃了选择权的王琦瑶,即便被动的获得了爱情,也无法永远的拥有,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物本身的性格就有悲剧性的因素?抑或仅仅是一连串偶然所导致的“非如此不可”?虽然原文中,瑶瑶是死了,舞蹈中,最后和眼睛兄天堂共结连理。但是这就是真正美好的结局么
在米兰昆德拉笔下,萨宾娜遇到了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对她很温柔,做爱没有暴力的人,回答问题也无比温柔。躺在床上的一刹那之间,萨宾娜忽然意识到,这种(看似温柔其实却早已丧失原始冲动的)男人,已经丧失了爱她的权力,虽然好像是男人在选择萨宾娜,但是萨并没有赋予他这种追求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是谁有权利选择谁?王琦瑶和眼镜程先生最后天堂圆满,难道一生懦弱没有冲动的程先生,就是我们认为的、瑶瑶的最好的归宿么?当我们在自己的理想中给遥遥安排了一个男人做最后归宿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了女主角的真实感受?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一个已经死了的、虚构的历史的人物上时,是否是对历史和死者的不理性?虽然瑶瑶是虚构的人,但是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个像她一样遇到男人出卖感情无力选择生活,一生潜意识中郁郁寡欢不能释怀的许多个=的“她”?(我忽然觉得我很像赵本山演的那个男妇女主任

)
毕竟编剧和导演把作品演绎出来了,作品的实验性也表现在几个历史事件的渲染和自我的嘲解上,编导和导演怎么理解历史是第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理解原著是第二个问题,只是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具有个人主义的色彩,皮亚杰提出图示概念,人们的理解必然居于一系列的个人的先验经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理解也不可能一样,我无法用自己的想法强迫编导和导演接受某种我的理解,正如编导和导演无法使我接受他们的理解,即便理解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真正的历史。
书写文学作品的作家,或者说小说家,往往大都有春秋笔法的特点,书写同时不忘援引众人皆知的背景和常规故事,仿佛,书写受众接受的事实,就能够真正的接近某些真相,讲述我们心里的想法,就能够真正和观众有所共鸣。回来的路上我没有怎么说话,回到电脑前正在迷迷糊糊的咀嚼着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时候,随后想起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话,米兰昆德拉的这个书也是讲的男女情爱的故事,但是让人物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超过了对于情爱的追求和保护,我想,不同的民族对于爱情的理解,或者准确的说,是对爱情理解的方式不同,可能男人和女人各自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还不是很适合来表达王琦瑶生命里的轻
毕竟中国人是含蓄的,有些话是不愿意主动说出口的,往往要通过其它的行为有所表示,这就出现了比如以前某个场景,女的喜欢男的,但是很含蓄,不好意思说,就往往很不含蓄的,用其他方式来大幅度的表示一下,好似国标舞充满张力和弹性的动作,正好能适合我们在不愿意直接诉说之时,夸张地进行表达。但是这种表达,不是站在客观的基础上的,是充满感情和主观的。如果是站在客观基础上的表达,就不会忌讳什么,亚里士多的人为人有“真正的理性”,这种客观表达一旦存在,那没有任何非理性因素的客观表达,实际上没有任何遮遮掩掩的必要。只有主观的非理性的表达,才需要“不好意思说出口”“话在心头口难开”。
可是我们缺少的不是有话没话的问题,而是怎么表达的问题。或许可以假设,是脑子中先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话,我们才不得不选择非理性的含蓄表达,这是“一定得这样”的必然;但也可以假设,一一旦我们有了另外的理性真实表达的表述方式,我们脑子中也会反过来根据理性原则来考虑问题,然后再说话。
其实绕远了,回过头来还是对于作品讲故事的方式的不同理解。文学内容是艺术作品的核心,缺少真正有思想和客观的内容,这个艺术作品也只能够流于一种感情的含蓄的表达,以及在这种非客观的表达基础上,自然也会遇到的非合理的事件、与男人的非合理的结果,以及更多的非合理的一系列相关因素的结果。尽管这只是我对作品讲述方式的理解。
我的朋友在舞台上表演的很好,不做作,非常真实,对于一生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可以挖掘的经历,衷心祝贺她

。因为这段时间在准备写一个很变态的论文,所以这个期间的变态文字、日志也就拿来练习想象力了,可以当做是办公室坐久了,用无聊的话,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吧

。
ps,推荐大家听听贝多芬的op135《非如此不可》,对于音乐中的形式主义,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