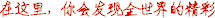2009年,值得纪念的事情比较多。
什么是最好的纪念?反思。
请看下列几大关键词或称几大个案
一、
民间舞和“代表性”有什么关系呢?不看不知道。
潘志涛在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的“综述”里说,1954年即老舞校初期,“中国民间舞只能陷入‘代表性’民间舞的尴尬境地。”
明文军在《舞蹈艺术》1993年第1期上说:“于是,将中国民间舞隶属于中国舞剧教学体系,一属就是30年。”
赵铁春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上说:“在当时,中国民族民间舞只能沦落到附属的地位,只能陷入‘代表性’的尴尬境地。”
根据潘/明/赵的以上表述,今天的民间舞学科在半个世纪中倍受屈辱的惨痛经历应该讲既是一种说法,也是一桩历史真实。
可是,另有一种说法。刘友兰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上说:“在我院,选用的课堂训练教材,包括五个民族、八个地区的民间舞。由于课时限制,不可能对每个民族的舞蹈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全面学习,于是就形成了代表性的教学体系。”
如是,此处的“代表性”和其他的舞种或体系没有关系。它仅止是针对民间舞学科自身的性质、内容与方式而言。
话说到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如果前三人说的对,那么今天的民间舞学科的地位已经天地翻覆!其间的功劳很该大书特书。
如果后一人说得对,那么今天的民间舞学科在“代表性”这一点上与55年前并无质变。所以,它依然是“附属”的和“尴尬”的。
总而言之,别人把你看成、当作“代表性”是一回事,你自己是不是“代表性”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本来就是“代表性”,人家也把你看成、当作“代表性”,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二、
今天的“古典舞系”或“古典舞学科”在自身发展史上的名称虽然比较乱,但是55年来基本上是在“古典舞”与“民族舞剧”这两种称谓上来回替换。
对于这个“正名”的重大问题,李正一在2008年接受访谈时的说法很精到很幽默。其大意是:我们心里想的一直是民族舞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古典舞了。
时至今日再去翻查到底是谁想出来、又改回去并死活坚守这三个字已经没有意义。要命的是这么多年了,我们居然始终钟情于或者说起码是容忍且待见了那“古典”二字,而这就百分之百的证明了:在我们的头脑里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深重之极的“贵族想象”。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说他本来姓赵,就像春晚上的赵本山说他老爷也姓毕,还有在马路边烙饼的常标“宫廷”的字号等等。
其实好听不如好干。“民族舞剧”是实事儿,说到底是个好不好的问题;“古典舞”是概念,人们总是劈头就问是不是?最后才想起来没有公认的定义。我看还是再改回来叫“民族舞剧系”吧,那样最少可以叫那些整天拿“古典与否”添乱的闲人们彻底闭嘴!让一拨一拨的大主演们想跳什么就跳什么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三、
潘志涛老早就有一句名言叫“这一个”。当时不懂,后来听研究生们说“这一个”的出处是黑格尔!于是五体投地。原来潘老师的西学底子了得,过去真是“狗眼”了,罪过!
此次翻检文献,就看到其原文发表在《舞蹈信息报》1991年8月1日,潘志涛说:“我想强调的是:‘这仅仅是我们的这一个,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四年来,我们就认识了这么一点,也就做了这么一点。”
再找黑格尔的原文,却先看到了恩格斯的“转引”与肯定。原来研究生们的资讯都是在《马恩论文艺》的课本上得到的。几下子一核对,无论是黑格尔的原意还是恩格斯的用意,反正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在谈主体与对象,个相与共相,现象与本质乃至“典型性”的问题。
据此,潘志涛的“这一个”同黑格尔的“这一个”一无学术关系,二无逻辑关系,只是在字面上碰巧一样了而已。
四、
“学院派”这个词现在几乎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同义词。我们自己用的同时希望别人也用,我们自己用的时候难免沾沾自喜,别人用的时候我们的虚荣心会得到一定的满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无论是自慰还是被安慰,在这个词里总是潜伏有某种揶揄、调侃、自嘲甚至是反讽的意味,唯独找不出一丁点自主、自勉、自律乃至自强的劲道。
于是便想要查查这一说法的出处。
现已查明:“学院派”是于平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上详细诠释出来的一个具有多重限制的说法。
限制一:主指创作活动。限制二:并非仅指舞院的创作。限制三:“学院派”的本质在“学者化”。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于“学院派”一词的理解和于平的初衷大相径庭。
误读一:凡是舞院人,就是学院派。误读二:凡不是舞院人就不是学院派。误读三:既然已经“学院派”,那么自然“学者化”。
据此,所谓“学院派”确实不能再作为一个概念或者实体而继续存在下去了。
另外,舞院内部最爱用“学院派”字样的是民间舞,即:“学院派民间舞”。我个人认为加了那三个字没帮上什么忙,反倒添了大乱。
五、
旧的词汇走了,新的词汇来了。
2004年校庆时段,“最高学府”一词被广泛传播。无独有偶,新词/旧词里都有一个“高”字。当然,这后一个“高”字现在也站不住了。因为舞研所有博士研究生,咱们只能招硕士。所以,我们不是“最高学府”而是“次高学府”。
话又说回来,大学应该以“学术为本”不应该以“技术为本”,所以,“高精尖”的衰亡与“次高学府”的兴盛正合逻辑反比。
归纳以上五节,希望读者们可以概括出某些经验和教训。
至于撰写这篇短文的初衷呢,原本是想从哲学、心理学或者教育学层次上,为我们学院的“主流话语”做一点分析性的研究工作,结果却连一点学理上的依据都联系不上,只好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