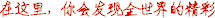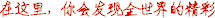T:对。山田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对电影的控制让人佩服,和他的合作很愉快。《黄昏的清兵卫》原来是小说家藤泽周平的短篇作品,黑泽明生前曾有意将其搬上银幕,但未能如愿就往世了,山田先生代黑泽明完成了这部作品。黑泽和子是黑泽明的长女,她负责《黄昏的清兵卫》的服装设计,相信也能体现出乃父的精神和画面追求。
现代舞大师田中泯专访 舞踏是对身体的革命
舞台上的布景很简单,只有枯山般的石头,一摊也许象征河流的水,台阶上有一只孤零零的箱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演出一开场,一个飘渺的声音,逐渐响起来,越来越响,几近让人耳聋。接着,从水泥柱后面缓缓走出一个老者,裹尸布一般的躲青色和服将他缠住。他像一个来自地狱冥间的死者,佝偻着身体,动作极慢,雀爪般的双手无助地挥舞、探寻、触摸。“他”没有姓名,演出没有台词;他开释着身体,演绎着内心对生死的感慨。
年过六旬的日本现代舞大师田中泯是舞踏艺术的第二代宗师。10月底,田中泯来沪演出,这是下河迷仓“越界艺术节”的重头戏。演出不卖票,但吸引了大量观众。田中泯的演出都是即兴、片断的,从不排练。他总是随音乐、环境起舞,用肢体诠释内心以及对生死的感慨。
演出中的老者就是日本现代舞―舞踏的第二代宗师田中泯。在第一代宗师土方巽往世和102 岁高龄的大野一雄退隐后,年过六旬的田中泯已成为舞踏的领军人物。
舞踏夸大由内而外地探索身体深处的能量。之后,舞踏致力于呈现死亡的姿态,表达亡者在永恒的寂灭中重蹈毁坏与死亡。在这层意义上,舞踏也被称为“暗黑派舞踏”,是一种黑暗的仪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舞踏传进欧洲,对欧洲现代舞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83年前后,舞踏由欧洲再回日本,掀起了比上世纪60年代更深邃的影响。就在那时,田中泯拜土方巽为师,致力于舞踏艺术。
舞踏(Butoh)是一种肢体表现强烈的新兴舞蹈,产生于战后的日本。当时的日本反战、反美,受此影响,日本舞蹈界一反过往追求西化、奉西方舞蹈为圭臬的信念,开始重视日本人身形矮小、无法淋漓尽致地表现芭蕾修长线条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舞踏之父”土方巽找到一种原始自然的表演方式:舞者周身敷抹白粉,弓腰折腿,蠕动缓慢,或满地翻滚,形容丑陋,表情悲痛。
假如说由于舞踏过于小众,田中泯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凡是看过《黄昏的清兵卫》和《隐剑鬼爪》的观众一定会记得他。田中泯在59 岁时,应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邀请,在电影《黄昏的清兵卫》中扮演与清兵卫决斗的武士余吾善右卫门。因在该片中的出色演出,田中泯获得第26届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新演员奖、第76 届电影旬报最佳新演员奖。
现实中的田中泯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势。他坐在下河迷仓休息室的沙发上,不停地吸烟,热情地招呼记者在他身边坐下。他身上那件皱巴巴的躲青色上装简单到了极致。他自称是农民,一个在舞踏艺术中默默耕耘的人,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唯有艺术才能让他心动,并且完全地投进其中。
B:对此次上海演出,你感到满足吗?
我的舞台没有一定之规
T: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从开始到结束,把舞跳完。
T:我倾向于在室外演出,由于在室外,观众就能和我一起感受同一片蓝天、吹拂的风和夜晚的星空。假如观众和我的感受一样,就更能理解我的身体语言和内心。
B:上海演出了两场,一场在室外,一场在室内。你更喜欢哪场演出,为什么?
B:你的演出非常“黑暗”,黑暗是否是舞踏最核心的部分?
B:在你的演出中,舞蹈是即兴的吗?
T:每个人对舞踏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来上海演出前,我希看自己能轻快一点,但是当我站到舞台上,就轻快不起来了,我不自觉地沉重起来,由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T:几乎都是即兴的。
B:但是音乐和舞蹈很贴切,音乐应该是事先设定好的吧?
T:事先我没进行任何排练。音乐设定了一种情绪、背景,我只要将自己融到音乐中往,幻想出一个世界,我在那个世界之中,也就在音乐之中。这也许就是你所说的“贴”。
B:每次演出,舞美都这么简单吗?
T:我从不重复自己,每场演出在结束确当下就结束了,所以今天的舞台布景只是今天的,并不表示明天我也会这样简洁。我的舞台没有一定之规。
我的作品都是片断
B: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舞踏?
T:舞踏在上世纪60 年代风靡日本,在当时是一种流行文化的象征。1983 年前后,当日本的舞踏影响了欧洲,再从欧洲回过头影响日本时,我才成为这门艺术的忠实信徒。我的老师土方巽先生对我说,舞踏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是精神的载体。
B:你的老师土方巽是舞踏的第一代宗师,你是怎么和他结识的?
T:有一天,土方先生忽然来看我的表演。当时我一直在舞蹈,但没有工作。我最初学的是欧洲芭蕾,后来学了美国舞蹈。我要找寻一种适合我的身体和灵魂的舞蹈,但接触了很多舞蹈之后,都没有找到回宿感,直到我看到土方巽先生的作品,深深为之震撼,并毅然决定投身于舞踏。
B:你和大野一雄有没有交往?能不能评价一下他的表演?
T:我和大野一雄先生没有任何交往。我不能对一位前辈进行任何评价。我看过他的演出,大野一雄先生做的是完整的作品,那是他一生的目标。这是我和他最大的不同点。
B:你做的是什么作品?
T:我的作品都是片断。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不会做一个完整的作品。
B:你曾说“有一部分的舞踏表演是危险的”。在数年前,你在表演时,从二楼往地上跳,你觉得危险是舞踏艺术中必须的吗?
T:有时候,危险是必须的。危险只是相对传统意义而言。舞踏将身体解放出来,这是一种革命。比如残疾人的身体固然残缺,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低人一等。有时候,他们比正凡人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比正凡人更先觉地熟悉到控制身体的必要性。而舞踏的舞者所要完成的,实在就是身体的控制和革命。
舞台比电影更自由
B:你先后参演了《黄昏的清兵卫》、《隐剑鬼爪》等电影。你觉得电影和舞台表演有什么不同?
T:简单而言,在电影中,我们总会细分各种艺术手段,而舞踏就是要打破这种分类,把各种艺术混杂在一起,摆脱束缚,让身体自由地、自然而然地在舞台上完美演出。
B:你第一次登上大银幕,据说是山田洋次请你出山的,是这样吗?你对他的印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