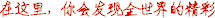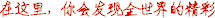近年来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使大型舞剧的创演成为活跃的舞台艺术形式之一。但繁多数量生产中又暴露出一些剧目因仓促上马而在艺术质量上的粗糙甚至欠妥之弊,片面地拼凑地方舞蹈元素、过度地追求视觉冲击力、夸张地显现不切内容的技巧、忽视形式与内容的契合、弱化戏剧结构力和整体艺术美感等弊端。这就使从1939年《罂粟花》就开始为中国民众所关注的民族舞剧创新突破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对象。作为世界上创作舞剧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后就有500余部),民族性征或物化形态的舞蹈元素融会无疑是中国民族舞剧突破的关键所在,《宝莲灯》、《鱼美人》、《小刀会》、《丝路花雨》、《文成公主》、《大梦敦煌》、《野斑马》、《丝绸之路》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多以其不同的题材寻得了突破,如《宝莲灯》的江南民间舞素材、《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的敦煌壁画“S”动作体态、《野斑马》的“仿生与拟人”创新型肢体语言等。从既往成功舞剧创演中汲取经验并结合时代性综合舞台艺术美需求,舞剧《赵氏孤儿》、《浮生》、《昭君》、《孔子》、《莲花》、《戈壁青春》、《仓央嘉措》等剧在民族性征的突破上做出了一些较为值得思考的探索。
首先是对集体舞的重点突出。从先秦《大武》等“六代之乐”开始,中国古典舞蹈就非常重视集体舞的运用,《浮生》就是较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手法的现代民族舞剧。它在《序》、《浮生忆》、《浮生门》、《浮生却》、《浮生难》、《浮生弄》、《浮生烈》以及《尾声》等段落都以各种形式的群舞方法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在日本侵略者的欺压下穷困、愁苦、悲惨的生活状态,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块面舞蹈场景展现了“浮生”的戏剧主题。群舞在剧中占70%左右的比重,是近年来此类舞剧创作中少见的大胆尝试。该剧艺术总监、舞蹈家刘炼认为,群舞的大量运用除了继承中国古典舞以及舞剧的传统手法之因外,还有《浮生》表现的自身内涵挖掘之需,它以或整齐划一或各自形态的舞蹈织体语言,旨在渲染东北芸芸众生从被奴役到觉醒的戏剧线索,从压抑到释放的情感发展过程,也较好地利用大型舞剧的形式锤炼了师生的实践技艺。群舞的大量运用在近年来的舞剧创作中呈上升趋势,它并没有弱化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反而以更为集中的篇幅突出了主角的技艺和戏剧张力。
其次是对地方性民间舞蹈元素的融会。在民族性征凸显的当下,舞蹈语言的地方性逐渐受到重视,各地也都在竭尽全力地致力于地方舞蹈语言的解构与重构,以适应现代舞蹈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仓央嘉措》、《戈壁青春》、《孔子》、《浮生》等剧都以其不同形态的民间舞蹈特性引用而具有亲和力。《浮生》以东北舞蹈的泼辣特性为主法而将大块面的群舞予以渲染。它并没有标签化地直接引用东北如秧歌等民间舞蹈身段,而是提炼其中的踢、踏、顿等步法,凸显了内在的“顿劲”、“利索劲”、“艮劲”精髓,从而不再是东北秧歌等民间舞蹈的程式化、表层化的呈现,在利于戏剧化表现的同时,也非常适宜于现代审美的需求,赋予地方舞蹈元素的时代气息。这些处理手法在《浮生趣》、《浮生梦》、《浮生凄》、《浮生遇》、《浮生离》等三人舞、双人舞段落中有着较生动引用,既展现了地方风格又推动了现代舞蹈的技巧观赏性。
再次是对戏剧性的凸显。舞剧不同于舞蹈的特性之处并非仅是长短的外显形态,而是着力于戏剧张力的营造从而带给人视听的震撼。但近年来舞剧有诗化、片段化等弱化戏剧整体性布局的倾向,如故事线索的隐晦、高潮及其冲击力的不明等,它放弃了舞剧所擅长的主线、辅线布局。刘炼讲到戏剧构思时强调,主线要凸显粗线条,要能给人以直观的刺激,辅线要彰显细腻性,在辅助主线推动的同时要给人以抒情的延展性。《浮生》以回忆的叙事线索将老妇人关于动荡年代的回忆一一串联,战争致人分离、死伤的情感悲壮,最后再次回到序的开始场景,统分结合,首尾呼应。既然是回忆,就可以就既往故事中的精要,这是戏剧铺设的“巧思”之所在,也就使看似片段化的舞剧板块紧密相连。藉此,《浮生》较好地注意了整篇的高潮营造,还在每一部分的小高潮的预设上注意了整体与局部的平衡关系,这就能始终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音乐主导也是《浮生》戏剧性强烈的重要一环,董乐弦以极具现代戏剧紧张度的和声与配器,为舞剧点燃了激情,烘托了东北抗战中浮萍飘零的民众的凄苦。
紧扣时代主旋律,深挖民间舞蹈元素,善用戏剧张力,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系列舞剧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上进行了有效地引导,给各地、各级的创作导引出突破口、着力点,将艺术性进行了国家层面的引领与设计,《浮生》、《赵氏孤儿》等剧的震撼上演就是扇扇打开的窗户,演者、观者享受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