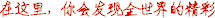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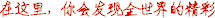

您当前位置:华人舞蹈网_体育舞蹈-体育舞蹈视频 >> 舞蹈资讯 >> 国内资讯 >> 浏览文章
舞剧《云南的响声》里有一个唯美的镜头:手指捏成雀冠形状的杨丽萍提着裙摆翩然出场,在她身后一群小孔雀以同样的姿态紧随其后、次第而出。这似乎是一种艺术传承以及不竭泉源的象征。
这群小孔雀很幸运,她们不再需要从芭蕾学起,不需要担心在尽情跳家乡的舞蹈时,被认为“太土了”。因为她们的杨老师,甚至可以拎着一个菜篮,走进名牌车展的现场。她们毋需再经历一个特立独行的舞者曾经尝受的艰辛,不需要在舞团前途未卜的时刻,当众落下心酸的眼泪。但是,也许她们就因此会失去,一个伟大的舞者应该接受的一切磨砺。
2012 年8 月,杨丽萍即将推出全新舞剧《孔雀》,据说这部由宝马独家冠名的舞剧讲述的是“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是一个关于生命、成长、人性和爱的故事。无疑这会是一部带有自传意味的舞剧,凝聚着杨丽萍本人对生命的感悟,这更是让人对这台据说完全新鲜的舞剧充满了遐想。
事实上,这个不老的精灵本身就是一部舞剧——西方人眼里她是来自东方的孔雀公主;彩云班的学员眼里,她是把自己从乡里带到城里的杨老师;在时尚的眼中,她是一则不老的传奇。2011 年底,一部讲述当代中国人梦想精神的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物志- 梦想篇》在全国26 家电视台的《探索》栏目中播出。在这部宝马与探索频道合作共同制作的写实风格的系列片中,作为片中中国梦想人物的代表之一,杨丽萍被称为 “以舞蹈传承文化血脉的精灵”。
从当年艳惊四座的《雀之灵》到今天万众期待的《孔雀》,她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巅峰舞者。在她身后,有《云南映象》团队,有彩云班,有传承原生态民族艺术的天然使命,正是在这条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杨丽萍完成了一个绝顶高手到一代宗师的蜕变。
一个舞者和一代宗师之间如有差别,那么就在于,后者将自己放入了一个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确定了自身的艺术坐标,而在这个坐标前后,艺术史会因此增加了厚度。
关于孔雀的故事
昆明艺术剧院的舞台上,高高地挂着《孔雀》的海报,事实上,无需任何宣传,2012 年春晚上的绚烂开屏已经惊艳全场,据说《雀之恋》正是《孔雀》中的一个片段,神秘的《孔雀》露出了冰山一角,却已足够为这部即将首演的舞剧带来万众期待。《孔雀》的排练尚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杨丽萍已经收到了140 多场演出邀请,有的演出商甚至已经直接把钱打到了账上,与十年前需要到处走穴筹集经费排演《云南映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孔雀》的成功似乎已经没有悬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也许是因为早在因《雀之灵》一举成名的时候,孔雀舞已经成为杨丽萍的独门绝技;也许是因为与高成明等现代舞编舞和舞蹈家,三宝、叶锦添等著名艺术家的合作使《孔雀》的主创团队更加强大;也许是因为江湖传言,《孔雀》是54 岁杨丽萍舞蹈生涯的收官之作。尤其是最后一个原因,更是引来媒体各种各样的揣测。杨丽萍要离开舞台了吗?
在舞蹈这个吃青春饭的行业里,在舞台上活跃四十余年长盛不衰,杨丽萍可谓是一个传奇了。早在十年前,已经有人频频问她:“还跳得动吗?”今天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她仍然一脸坦然:“我们生下来就要面对死亡、面对衰老,这是事实。我觉得舞台生涯一定是有限的,肯定要在恰当的时候离开舞台,比如说《孔雀》,《孔雀》是我自己舞台表演的一个总结。”但在杨丽萍看来,不在舞台上表演,不代表舞蹈生涯的结束,“舞台只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其实舞蹈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跳,不一定是表演性质的,可以是自娱的,可以是自己的抒发,不一定非得面对观众”。她不喜欢别人称她为舞蹈家,她觉得自己是生命的舞者,或者就像很多人说的,她是一个为舞蹈而生的女人。
1971 年,杨丽萍11 岁,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的时候,被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她开始跟着西双版纳歌舞团走村串寨,命运一下被改变。9 年之后,她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从进入歌舞团的第一天起,她就和别人不一样。作为一个从没上过舞蹈学校的舞蹈演员,在学院派眼里,她的基本功一塌糊涂,劈叉都劈不直。而在后来回顾那些按照芭蕾舞动作训练的日子时,她曾说:“不久,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因此,她拒绝了团里安排的一切舞蹈练习,不再和别人一起练功,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她总是白天睡觉,等晚上教室空出来再去点着蜡烛跳舞,一跳就是一个通宵。
1986 年杨丽萍创作了独舞《雀之灵》,为了制作服装,她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但团里不同意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就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获得了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杨丽萍本人站在了中国舞蹈的巅峰。
一场没有一个观众的演出
冥冥中一切皆有缘法。1989 年,摄影师肖全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关于杨丽萍的报道,他对身边的家人说:“我将来一定会给这个人拍照。”那时候,杨丽萍刚刚因为一曲《雀之灵》一举成名。三年之后,肖全意外地接到杨丽萍的电话,希望他为自己即将赴台演出,拍摄一组海报。这就是那张著名的站在长城上的照片的由来。肖全回忆说:“那时候,她站在长城的城垛上,脚下就是百丈悬崖,手中抱着一团绸带,我大喊一声‘放’,那绸带就被风吹得紧紧裹在了她身上,美得像仙女一样,好像一眨眼就要乘风飞去。”后来,肖全把自己拍摄的杨丽萍经典图片集中起来,在北京做了个展览,还发行了一套明信片,走到哪儿就签上名当名片发给别人,封面就是用的这张照片。
肖全跟踪拍摄她长达20 年。肖全说:“三毛和杨丽萍是我拍过的人中最接近上帝和自然的女人。”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995 年,杨丽萍投资700 万拍摄电影《太阳鸟》,肖全跟着剧组来到杨丽萍的家乡──云南西双版纳。“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杨丽萍舞蹈的隐秘来源。”肖全看着杨丽萍和老乡围坐在火塘边,一起大口喝酒,一起吃手抓饭,一起围成圈跳舞,买了老乡的布做裙子,看到老乡的菜篮子好看,当场就买下来,把篮子腾空,就装上自己的东西走了。“她的舞蹈就是从这片地里长出来的。”他还记得拍摄《太阳鸟》时遇到的困难,一些群众演员因为待遇问题闹着不干了,“我想去安慰一下她,可是我看到她坐在烈日下,脸上没有愤怒,只有理解和无奈,我忽然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不需要安慰。”
2001 年,肖全来到昆明,看到杨丽萍在一间简陋的练功房里带着一群孩子排练舞蹈。“我才知道她用自己纤细的肩膀扛起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本来有一个老板要赞助的,但看了节目后就撤了,他说:‘太土了,这怎么能赚钱?’”这一次,肖全拍下一张照片,杨丽萍双臂平举,头向后仰,长发披散在手臂上。“那一刻,我觉得她进入了大师的状态。”
境界的提升总是来自于艰苦的蚕蜕。排演《云南映象》的那三年,杨丽萍不再只是一个只需要跳好舞的舞蹈演员,最艰苦的时候,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一个人要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她开始拍广告,走穴演出。有一段时间,排练完了要走很远的路回郊区宿舍,而她当时的住处除了一张席梦思,没有任何家具。她也不懂照顾自己。大冬天屋里没有一丝暖气,只能披着被子打哆嗦。
最困难的可能不是排练,而是《云南映象》的首演,那是一场没有一个观众的演出。当时正赶上2003 年非典,原定于昆明会堂的演出差点被取消,几经周折,也只能演一场,而且没有观众。演出完,全体放假几个月,前途不明,可能就此别离了。大家去昆明饭店吃自助餐,一直没事人似的杨丽萍开始哽咽,跟着台下的演员们哭成一片。熟悉她的人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泣不成声。
很多人在当年的8 月再次归队,也有一些人没有再回来,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通。有些人住的地方,离开有电话的街子至少要翻三四座山。杨丽萍带领这些村寨里来的演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的演出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云南映象》团队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这台节目至今已经连续演出十年,近4,000 场,出了三本书。杨丽萍说:“《云南映象》要一直演到30 年,因为一个作品演不到30 年就不算好作品。”她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见证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云南映象》之后,杨丽萍又先后推出了《云南的响声》、《藏谜》等作品,同样大获成功。至此,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从武林高手到开宗立派,杨丽萍的舞蹈生涯走过了40 年。
觉醒与传承
觉醒是杨丽萍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汇。不过在她看来,觉醒没一般人想得那么神秘,“觉醒就是认识自己的能量,认识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自己能做多少事,觉醒就是看到一只燕子划过水面,有感觉。”
她把自己称为新型的民间艺人,“最早的音乐是猿猴叫,最早的打击乐是心脏的跳动。有一个舞蹈叫左脚舞,那是因为最早跳这个舞的老艺人是个瘸子。但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创造,一个村子可能几代人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看完的东西能直接转换成舞蹈语言。文化不是说戛然而止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比如说像《雀之灵》、《月光》,再过一百年就是遗产了。民族舞蹈不能在我们这儿就戛然而止,所以在我们这一代,我极力主张创造性,但是它的根基是不会变的。想让我变我也变不了,因为在这片土地熏陶出来的,它就有那个味儿,它不会脱离。”
与《云南映象》的原生态不同,新的舞剧《孔雀》完全是创作型的,但秉承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也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乐器上台。杨丽萍透露,《孔雀》里的口技会给大家带来震撼,这种新的形式在以前的剧中都没用过。《孔雀》里全部演员都要会口技,排练的时候吹起来震耳欲聋。
杨丽萍常常形容自己的舞蹈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在《云南映象》之后,她被称为文化的传承者,事实上,在舞蹈之外,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承上。
2012 年3 月15 日下午,杨丽萍坐在云南艺术剧院的观众席上,“杨老师,你帮我看一下!”一个男演员抱着月琴走上台,随意地用云南话对着台下说,自然地就像对着自家的邻居。台子的两边坐着一群半大孩子。这是杨丽萍和彩云班的孩子们在为当晚的节目彩排。这一天,杨丽萍与宝马公司合作举办“传承·绽放”为主题的发布会,宣布携手成立“云南映象艺术传承中心”,帮扶云南边远山区贫困青少年艺术教育,初期生源就是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彩云班”的188 名学生,他们全部是来自云南边远地区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其中46 人是非常具有艺术潜质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计划实验组成员。
杨丽萍欣赏的德国舞蹈大师鲍什·皮娜曾经有言,“我跳舞因为我忧伤”。而杨丽萍却是并不是因为撕裂式的现代苦痛,而需要舞蹈的宣泄,她说“我跳舞是因为我喜悦”,喜悦于四季、自然和生命的呼应。“JOY is BMW”(“宝马之悦”)作为一个西方现代企业的理念,恰好呼应了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哲学,东西方理念在此寻找到了恰切的贴合,也促成了一种当代文化生态链的良好合作。
就像那些被杨丽萍从村子里挖出来的舞蹈演员一样,彩云班的孩子也都是怀着一个梦想来到这里的。杨丽萍还记得自己当年一个一个从村子里挖掘演员,阿秀是为了买一头牛才来跳舞的,而阿桑木子前段时间跟她聊,他的梦想就是在城里拥有一套房子,更多的人只是希望工资高一点,生活好一点,他们不是什么英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养活自己。而在他们身上,杨丽萍看见自己的梦想。
“我想要把这种最古老的传统的文化,把它挖掘出来。我还希望它有一个特殊的剧场,特殊的学校,教学要非常准确,不走弯路,这些都是我的梦想。”杨丽萍在云南映象团队里收罗了不少奇人,比如拿起什么都能吹出音乐的罗罗拔四,比如创造新的烟盒舞的虾嘎,比如脑子里装着几百首乐曲的阿罗巴。她希望这些民间艺人能把自己的绝活儿传下去。杨丽萍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当年虾嘎来到剧组的时候,完全是零基础,在3个月到1 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变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表演者。现在,杨丽萍要用这种方式培养更多的舞者。
十年前,杨丽萍踩着树根,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去寻找《云南映象》的演员,那时候他们住在蘑菇房里,烧着火塘、打着莽鼓,现在都是瓷砖房了,村子里的年轻人也不再喜欢穿民族服饰,他们更向往山外那个文明的世界。“不是我改变他们的,这是世界、所谓的文明在改变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原生态的歌舞文化能不能完整地保存,甚至保存下来是不是有意义,杨丽萍说,这都是问号,“我不想那么多,只是做,能做多少做多少。”
无论如何,比起以往的任何时候,这都是最好的时光。至少彩云班的孩子已经不需要再从芭蕾学起。他们可以尽情地跳家乡的舞蹈,而不必担心“太土了”,就像那个从老乡手里买来的菜篮子,当杨丽萍挎着它走进名牌车展的时候,网友评价说,这比LV 气场更强大。
杨丽萍理想中的舞台是这样的:观众席是泥巴糊起来的,红泥,不会龟裂、不会坏的那种,凳子是那种树枝搭的,在一些火塘边上,观众坐的地方,都有麻绳拉着,可以直接从井里打水。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坐在这样的剧场里看《云南映象》以及《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