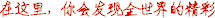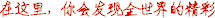台湾舞蹈家林怀民曾说,如果云门舞集可以从头做起,他要弄很小,越小越好,就像中国现代舞团陶身体。“大陆现在我最看好的编舞家是陶冶,他和太太段妮两个人编一个舞,在地上爬来爬去,30分钟,站都没有站起来。他们说为了这个舞,两个人死爬活爬地弄了10个月……他大概是全世界年轻编舞家里唯一在下功夫的……别人都是流行什么搞什么,他没有。”
林怀民说的这部作品,是陶身体剧场的现代舞《2》。陶冶编这个双人舞时想要表达的不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是在性别上有一种超越,做出一种有质感的纯肢体舞蹈。类似的作品,还有现代舞《4》。
8月3日、4日,陶身体《数位系列2&4》将在国家大剧院做首次国内公演,这也是陶身体在国内极少数的售票公演之一。《纽约时报》首席文艺评论家阿拉斯泰尔·麦考利曾惊艳于陶身体戏剧性的舞蹈张力,“舞者对身体运动有着控制和强大的驱动力。”
“我的作品没有主题”
陶身体剧场在2008年3月诞生,当时只有陶冶和王好两位舞者,没钱,没作品,没场地。同年8月,随着段妮的加入,舞团开始稳定,排出了第一部作品《重之三部曲》。这部作品让陶身体在国际上发了声,《瞬间》、《2》和《4》则坚定了他们日后“身体研究”的方向。他们的肢体语言讲究“重心转移”和“失重”,在失重过程中还要有自己的重心,这就带来了一种视觉感极为不同的舞蹈方式。陶冶的编舞理念是强调动作本身即是意义,“让国外观众最吃惊的是我们作品表达的理念,我的作品没有主题,这种抽象的概念必须建立在非常强烈的视觉方面才能达到。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不到我的情感,但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陶冶说。
2011年,美国姑娘方美昂的加入,为陶身体在国际上的拓展起了不少作用。单就林肯艺术中心、悉尼歌剧院、美国舞蹈节这些陶身体曾演出的场所,便很能证明陶身体的水准。现在,陶身体每年会有8到10个艺术节的邀请,演出日程表也排到了2015年,是实实在在靠国外演出来维持生存的现代舞团。
但这一切,对回到国内的他们来说,没有带来任何回报和意义。陶冶的父母甚至建议他去上“春晚”,参选“快乐男声”。“我当时就崩溃了。”陶冶忍不住笑出声来。
“现代舞的环境不好”
北京近两年的现代舞演出环境和欣赏水平,常让不少京城以外的舞蹈爱好者艳羡,也常让人有轰轰烈烈的错觉。比如,7月北京会有“北京舞蹈双周”,8月、10月则有“中国舞蹈十二天”和“国家大剧院舞蹈节”,每月时不时也总有国际大团降临。陶冶身在其间,却并不那么乐观,这些热闹“就像个泡沫”。不只是国内剧场文化没有固定观众群,评论体系不完整,现代舞和观众的信任关系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多舞者在台上常常带着犹豫和惶恐。不少人来看现代舞只是尝鲜、看热闹。陶冶说:“国外也并不是都好。因为有太多演出、艺术节和舞者,不可能没有泛滥的恶俗。来看现代舞演出的也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年轻人更爱混酒吧。全世界的现代舞环境都不好。”
这两年陶身体在舞蹈界虽然名气渐长,在国内却基本没做过租场性质的商业演出。商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亏损。陶冶举了例子,适合他们演出的剧场租四小时便要3万元,还不包括灯光、舞美、道具、演员休息室和宣传的费用。“票房无法回收成本,国内又有赠票的习气,要不然现场很惨然,对演员的情感也是一种挫败。”让陶冶感觉困扰的,还有舞者的寻找。很少能有舞者安静下来去呈现他的作品,以及“忍受”至少要用半年至一年时间来感悟的前期训练。
唯一让陶冶感觉安慰的,是现代舞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能让他结识这个领域里其他一些有相似“阵痛”的人,比如音乐家小河、雕塑家向京、摇滚旗手崔健等。他们和陶冶有相似的认知,也曾带给他不少信任的力量。
“陶身体很用功,有不少新鲜的现代舞理念,作品也有用心在打磨,规模虽小,却也都精致。”相继担任过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艺术总监的曹诚渊,常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国内一茬茬冒出来的小型独立现代舞团,比如今年参加“北京舞蹈双周”的舞团就有50余个。他们的特质在于作品和新人不断涌现,有思想的激荡,但并不见得长久,有些夺人眼球,大多数默默无闻,昙花一现。
能像陶身体频繁去国外演出的独立舞团并不多。身体技术、舞蹈内容和国际代理人的缺失都是问题。雕塑家向京曾形容陶身体是这个坚硬物质时代里的“幸存者”,因为他们在国际上算是得到了一种沟通的话语权。国外舞评人在评论他们时,常常找不到既有的参照物,而不得不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评论方式。因为没见过,陶身体给了他们耳目一新的东方感觉。
“但陶冶也只能代表陶冶,不能说他代表了中国现代舞的方向,这样压力和包袱都太大。”曹诚渊说,“有号召力的大型现代舞团就像花园里的树,但花园里只有树肯定也不够,要有各个季度的花相继绽放和凋谢,才更能彰显一个地方对现代舞的包容能力。”国内现代舞的现状,只能说还在竭力开凿通往百花齐放的花园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