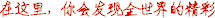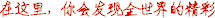安徽凤阳民族舞《花鼓灯》 CFP
杨丽萍《孔雀舞》CFP
一支《雀之灵》流传了20多年,傣族的孔雀舞也因着杨丽萍现代形式的表现而被更多人认识。中国民族民间舞就这样通过舞台表演被人们熟知。
原本在田间地头的民族民间舞该如何走上舞台?我们从源头开始,寻求答案。
雅化——从原生态走向舞台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源远流长,或为庆丰收,或为敬神祈福,或抒情自娱,民俗内涵丰富。
而其舞蹈元素被充分提炼并升华运用,进而搬上舞台,始于新中国成立前。
上世纪40年代,“新秧歌运动”点燃了民族民间舞舞台化的火花。戴爱莲、吴晓邦、贾作光等老一辈舞蹈家在充分采风的基础上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青蓝布为衣,对襟齐领,长可蔽膝身,以彩绣镶边,头挽发髻,配以银饰高冠。”淳朴自然,诸如《瑶人之鼓》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化形式引来众多喝彩。
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化即是“雅化”,是对民族和地区文化典型特征和情感的提取。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民族民间舞的主要类型是反映一个群体或者一个族群的情感,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明文军介绍,“像《东方红》大型歌舞,恢宏壮美的场面既传达厚重而苍凉的历史追怀感,又抒发对新中国的欢欣与满足,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及至上世纪80年代末,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化开始更多关注个人的人文表达,从情感向人物形象过渡。例如独舞《残春》,男子为青春的永远流失而痛苦遗憾,他扑倒在地,伸出手却什么也抓不住,感情饱满,形象鲜明,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而今,民族民间舞的雅化更是越来越多追求“人”的形象——这些演变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两难——民间性在舞台上流失
舞台化对民族民间舞发展有着毋庸置疑的促进作用。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教授潘志涛举例道:“近些年,山东三大秧歌的舞蹈创作及表演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和深度,正是得益于舞蹈专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加工、整理。”而历年春晚的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踏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民族民间舞总能大放异彩,各个民族特有的经典舞蹈动作深入人心。
犹如硬币的两面,舞台化在推动民族民间舞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忧心的情况。粗制滥造随意嫁接的现象比比皆是,过度追求舞台技巧、效果和服装的情况俯仰可见,脂粉味儿掩盖了乡土气息。2002年曾有舞蹈《碧波孔雀》,以艳丽的色彩塑造了一群动感十足的现代孔雀形象,从体态到动律再到形象本身完全改变了传统孔雀舞的面目,让人不禁要问:离舞台越近,是不是就会离本真越远?
一些民族民间舞的舞台表演中混杂着芭蕾舞、现代舞等其他舞种的影子,使得民族民间舞变了味。尤其是大量以比赛为目的的创作,更倾向于直接借用现代舞的高超技术来夺人眼球。青年舞蹈家刘岩指出:“这种所谓的同化其实是舞蹈语言中的病句,让人难以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
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认为,现在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表演缺乏艺术震撼力,过于苍白而与原本的民族民间特色脱节,原因在于编导们很少直接到民间进行采风和学习。明文军则坦言,创作者对自我过于强烈的关注,使民族民间舞的“魂”或者“气”,即其特有的文化性、民族性、民间性逐渐流失。
此外,在民族民间舞的教学中,缺乏对原生态舞蹈的强化,使得一些年轻学子误将课堂上抽象化教学化的舞蹈当成了民族民间舞的原貌。“更可怕的是,这些学生再到民间去指导当地的舞蹈创作和表演,以讹传讹,一定会对民族民间舞原汁原味的保存产生很大危害。”江东对此忧心忡忡。
寻魂——发掘民间最本真的精魂
对于解决民族民间舞舞台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舞蹈界、学界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深入民间、实地采风的重要性。
刘岩认为,专业的学子、教师及创作者们“必须实实在在去采风,去感受民族民间舞的本来面貌,去发现和发掘民族民间最本体的元素与精神”。
明文军认为,舞台化的关键在于把握民族民间舞的内在,“优秀的舞台创作能够抓住民族民间文化的魂与神,把握其特有的形态、神态、情态、动律及节奏,提纯出适合上舞台的动律和形象,如此不失本分又耳目一新,自然更容易让更多人接受”。比如,把原有形式加工后搬上舞台的《花鼓灯》;运用民间舞蹈素材创作的《一个扭秧歌的人》;或展示一个主题的《爱的足迹》《黄河儿女情》等,都是成功的“二度创作”。即所谓“源于民间、高于民间、既不失风味又科学规范”,这大概是舞台上的民族民间舞追求的最高境界了。“离雅的舞台更近并不会离民俗更远。”明文军说,急功近利才会远离根本。
明文军介绍,在发达国家,舞台表演的市场及社会定位层次分明。各种表演形式各自迎合其定位的观众群,各自繁荣互不干扰,这就保证了纯艺术健康成长。但中国民族民间舞并无明确分类,舞台创作既要迎合市场维系生存,又要符合艺术规律,显然是十分艰难的。治本之策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建立对我们国家民族舞蹈的自信心。